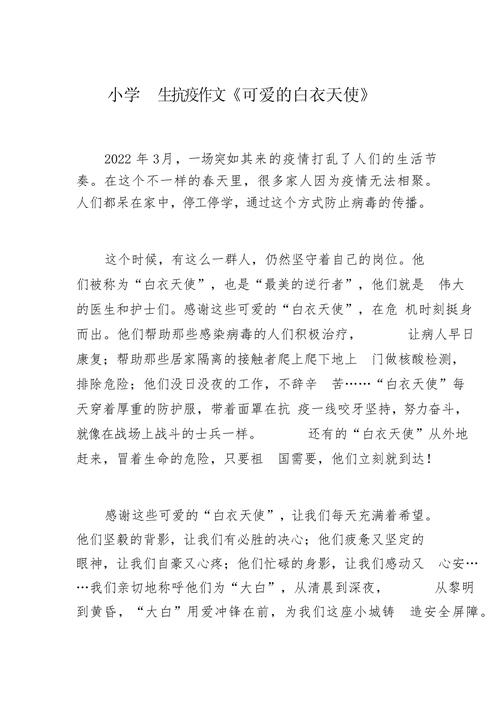2022年3月,在上海封控前一周的时候,我还在忙着抢菜,然而,真正致使我崩溃的并非是买不到东西,而是在居委会通知去领物资的那天,我处在队伍当中时,忽然发觉自己已然忘记了该如何与邻居正常地说话。
恐慌从抢菜开始
3月27日晚间11时,群猛地炸锅了。浦东要实施封控,此消息来得太过突兀。我目不转睛地瞅着手机屏幕,手指于各大买菜 APP 之间不停地来回切换,购物车里明明已全是蔬菜,可结算按钮却怎么都按不进去。凌晨一点时,我依旧在不停地刷着,明明晓得第二天六点还能够抢,然而就是不敢入眠。
翌日清晨五点五十分,我比预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开启 APP,手随即开始颤抖。当倒计时归零时那一刹那,页面出现卡死状况,待其恢复正常后,菜品已不见踪影。就在那一刻,我蹲于客厅地板之上,眼泪不由自主地掉落下来,并非因饥饿所致,而是源自内心的恐惧——惧怕接踵而来的未知状况。
楼道里的沉默邻居
处于封控状态的第三天,我头一回出门去做核酸检测,在电梯之中碰到了楼上的阿姨,我们经由口罩相互点头示意,没有任何人张嘴说话。回来之时又一次在电梯那里遇见,依旧没交流。实际上我特别想询问她家里是否缺少东西,不过我张了张嘴,最终愣是没有发出声音。
这种沉默延续了足足两周时间。直至有一日,我家的门把手上着一袋青菜,既没有纸条,也没有署名。我敲响了楼上阿姨的房门,她打开门看到我手中那袋菜,先是呆住了,而后隔着防盗门摆摆手讲:“不清楚,不清楚是谁放的。”然而我们全都知晓。
新闻看多了会心慌
进入4月上旬,那可是极难熬的时段。每天清晨一睁眼,首要之事便是查看新增出来的数据,而后开启各种求助帖子的浏览模式,一直刷到凌晨两三点钟,手握手机依旧难以割舍去放下。某一晚,瞧见附近小区存在老人断药的情况,躺于床上辗转反侧,根本睡不着觉,明明清楚自己没办法帮上什么忙,但刷消息的动作就是没法停下来。
接着我妈妈打来了电话,听到我声音异样,讲你别再看了,即便看了也没法解决。我嘴上回应知晓了,之后断电话仍旧持续刷着。那种感触十分奇特,仿若自我虐待,又好似是一种责任——我必须要清楚外面发生了何事,我不可以佯装若无其事。
一个人过生日
我生日是4月15日,提前一周就晓得蛋糕肯定没指望了。当天早上,我用最后两个鸡蛋煮了一碗面,坐在窗边吃着。楼下时不时有穿着防护服的大白走过,小区里没人喊喇叭,安静得吓人。
下午的时候,闺蜜打来视频电话,她所处的地方也处于封控状态,隔着屏幕为我唱起了生日歌,唱完之后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,只是那样看着彼此,她说,等解封之后请我去吃大餐,我说可以,断电话之后我又哭了,这是封控以来第二次落下眼泪。
解封那天没有狂欢
6月1日零点整,上海宣告恢复正常通行此讯。彼时我立于阳台上,听闻远处有人燃放烟花,马路上开始有车辆驶过之动静。然而楼下并无想象当中人群欢呼之景况,亦无人冲出门去拥抱一番。众人仅仅如同平常那般,下楼去扔垃圾,于小区里走上两步,而后返回家中。
就在那天,我特地出门去乘坐了一回地铁,车厢当中人数并没有很多,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,目光呈现出躲闪的状态,我发觉自身也不太擅长与人进行对视了,解封已然完成,然而有些事物似乎依旧没有被解开。
现在的后遗症
2026年2月,疫情已然过去了将近三年。我家的冰箱依旧习惯性地被塞得满满当当,购物车里始终预备着一份常温奶以及罐头。朋友讲我太过焦虑,我回应说这称作有备无患。实际上我心里明白,这是当年遗留下来的毛病。
去年双十一之时,我瞧见有人抢购几百斤大米,我的第一反应并非觉得这话夸张,而是心里想着:我是不是也该囤点呢?随后自己就笑了。那段日子留下来的不单单是习惯,还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绪,并非是害怕疫情再次来临,而是惧怕再次经历一回那种不清楚明天会是怎样状况的无助。
在什么时候,你会发觉,直至当下,自己对于往昔的那份情绪,始终未曾全然摆脱掉呢?